
科技改变生活 · 科技引领未来

科技改变生活 · 科技引领未来
诗人的天职,就是发现这种不同时代和同一族群所共有的人文传承,进而抛弃现世的判断,寻得永恒的价值。就此而言,诗歌的成就标志着一个民族意志与精神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张方马志强,甘肃陇东人。“70后”军旅诗人。创作的《走近日月山》《硕果的保护者
诗人的天职,就是发现这种不同时代和同一族群所共有的人文传承,进而抛弃现世的判断,寻得永恒的价值。就此而言,诗歌的成就标志着一个民族意志与精神所能够达到的高度。
——张方
马志强,甘肃陇东人。“70后”军旅诗人。创作的《走近日月山》《硕果的保护者》《忘不了妈妈》等上百首诗歌作品散见于《绿风》《诗潮》《西北军事文学》《新国风》《解放军报》等杂志报刊。诗作入选《鹰之击——大西北边塞诗选》、《草叶诗人》等多种诗歌选本。曾获“昆仑文艺诗歌奖”等10余个奖项。著有《西部碎片》《苍茫西部》等诗集5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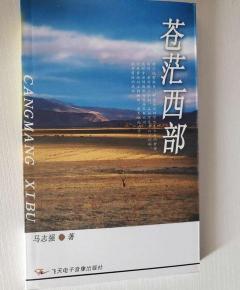
诗歌,尤其是军旅诗,因其具有阳刚、豪迈、激越等特征,描绘高山峻岭、江河湖海、大漠孤烟、金戈铁马等意象,被那些在军旅和曾经身在军旅的诗人们坚守,在诗坛独辟了一道壮美的风景,以其沉稳之姿、敏锐之态,占据了诗歌的一席之地。
苍茫西部纸为墨,高亢军歌映心声。生长于陇东大地的马志强,深受厚重黄土文化的熏陶,从军20余年,依然乡音未改、本色纯真,浑身充满着对祖国、军营和基层士兵的无限热爱,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生活闲暇勤奋笔耕,作品真挚而感人,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以《苍茫西部》为蓝本,对马志强诗歌创作进行梳理,会发现他在诗歌创作有着明显特点:第一,用真情直抒胸臆,体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属性;第二,善于运用记录者的独特视角,用诗记载或叙事;第三,注重新写实主义诗歌技法探究,完美实现了以诗托物言志。
第一,用真情直抒胸臆,体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属性
在诗集的第一辑《青春触角》里,首先进入眼界的是百行长诗《走近日月山》。他的这首诗歌,曾得到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诗人王久辛先生的高度评论:“诗写得极其有味道,诗中透出的那种毛茸茸的意味,读了实在令人叫绝。”
日月山是那样哀怨悲壮那样凄清/一阵唐朝悲歌的余音拖着沉重的心/在五千年的茫茫黄沙,千年的/天荒地老中寻找残存的痕迹——/发黄的史书中一只血迹斑驳的羽鸽/云端飘来一个血泪浇注的传说/埋葬杀虏征掠的战争,泥土/尘封的脸上两只转动的眼睛,穿越/历史的长河,一支让历史颤栗的悲歌……
——《走近日月山》
在诗中,诗人以在青海采访时路过的日月山作为倾听对象,然后神游九州、思飘万里,与唐朝的公主有一段关于“战争”主题的对话,可谓诗意精奇,点睛之笔随之而落:“战争,记载毁灭传播文明的途径/却无法让野心的当政者感到满足悲痛/把无辜的人卷入死亡,毁灭的/只有使人断肠的悲壮和/准备用人骨独奏的国殇……”
“战争,记载毁灭传播文明的途径。”仅此一句“诗魂”,就道出了“战争既可以毁灭一种文明,又可以使不同的文明不断交融”这一战争观,解语了历史发展与起源的奥秘。纵观历史进程不难出现,自从“阶级”出现以后,只有战争,才能摧毁旧社会,创造新纪元;也只有战争,既承担了创新的罪过,又肩负着推进历史重任。军旅诗人这样的总结,当属一种天然的使命与担当,更是直抒胸臆的完美体现。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读马志强的诗,听不到无病呻吟的蝉燥,看不到虚装伪饰的雕饰。极目之处,灵肉之山真切自然,爱憎之水泾渭分明,无论是谁,只有阅读,就能够从他的字里行间走进他真实的内心,时而如深沉大漠,时而如黄莺啼鸣,给人的冲击猛烈而不失稳重。
他笔下的《军人》:“无论那一座高山/没有你雄厚/无论那一条大河/都没有你磅礴/你只用一滴汗水/浇灌,庄稼/你只用一根手指/保卫祖国。”既讴歌了和平时期,当代军人的伟大平凡,也对胆敢犯我中华者,提出了态度鲜明、意志坚决地警告:“你只用一根手指/保卫祖国”,意象活泼、用词形象,真可谓诗意酣畅淋漓,用语入木三分,又饱含着对祖国、对军营、对军人的理解与高度赞誉。
再看《西部,士兵的年轮》:“滚滚黄沙/磨平戈壁的皱纹/手握钢枪的士兵/在孤独的哨所/消逝自己的风韵。”他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以诗进行展示,语言简洁、节奏明快,很现诗歌的厚重,字时行间,散发着一股陇原之子真挚的爱和纯朴的情。
首届中国十佳军旅诗人马萧萧也在诗集《苍茫西部》序言中评价马志强在诗歌创作中:“他把对西部与西北军旅的热爱、眷恋,进行大胆的想象、揣摩与描绘,当作生活的反刍,爆发出浓郁的情感。”
第二,善于运用记录者的独特视角,用诗记载或叙事
诗人写诗,其实就是用诗歌这种文体在进行心灵对话。每一位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同一座山,有着不同的形状特点,即使面对同一条河流,也会吟唱出不一样的声音。
在浩瀚的诗海中,比如黄河,就诞生了不同的佳句: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行路难·其一》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刘禹锡《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登鹳雀楼》
在诗人马志强的笔下,他的诗情到处别具一格,比如在他的第四辑《苍茫西部》中,他诗风凌厉,让人读来眼前顿觉一亮。如果说第一辑中用的是长矛和标枪,那么在第四辑则换成了短剑或者匕首这样的短兵器,“一寸短一寸险”,他在文字的短兵相接时,更加彰显了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底和非凡能力。尤其是他的《诗歌日记》,首先这组诗的标题很新颖,诗歌就是诗歌,日记就是日记,而他却用“诗歌日记”作题,颇有深意,亦有创新。
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中,作者介绍了这组诗的来历:当时他写这组诗时,正在原兰州军区政治部学习,冬日周未之晨,阳光温暖温馨,他在桌前一坐,突然灵感爆发,一气呵成做诗10首,题目统一记做《诗歌日记》。
如果拿他的短诗和长诗相比较,我认为短诗更近似在运用记录者的独特视角,用诗歌记载或叙事。因此,诗的意象更加集中,语言中也透露和弥漫着一股强烈的陈述的味道。
比如《城市》:“一首诗/一个鸟笼/两首诗/两个鸟笼/在都市的耀眼处/搭起一个个凉棚/花钱买一个/把小鸟放进去安家”。用短短的诗歌形式,就道出了城市的高楼大厦、人与人之间的浑然状态,在一个个钢筋水泥构筑的方框中,住着像“鸟儿”一样的“人”,他们晨出而做、日落而息,周而复始,年年如此……。
是幸福的味道、是家的思念、是寄旅的无耐、还是触手之间的老年……多种味夹杂、多种情感纷呈,不同的景遇者读此诗,都会产生不同的联想,这也许就是诗歌的“记载”“呈现”功能吧。
诗人也写到了《黄河》,他的笔下,黄河“你是一个羸弱的女婴/从小到大都被人看不起/城市把你抱在怀里/你就跌落了自己/失足后的/青春少女/从此不再坚守贞操”。三江源头、黄河清澈;爬山涉水,逐渐浑浊……
世人皆知黄河,但真正知道她源头的人并不多。黄河是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诞生的,而后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垦利县注入渤海。
在诗人的笔下,黄河从开始“羸弱的女婴”到最后“从此不再坚守贞操”的女性,看似是贬义书写,实际上对黄河的历程的一种担忧,黄河治理是一件大事,而大挖河堤、肆意开采、生态破坏在前几年是近乎疯狂的举动,如此理解诗意,方能明白作者书写的意图:心中担忧!口中呐喊!
还有一些短诗,比如“一张冷冰冰的脸/还有冰冷的躯干/不论生气还是高兴/倒下一个/有人开心有人哭泣一生/而你也只是清清喉咙/(《枪》),此类平而不谈、清而不浅的诗句,不禁让我想起了“以少胜多”、“精兵强将”等军事术语,这些诗歌语言如同一块块干粮,不乏营养,耐人咀嚼。
可以说,没有对人生的深刻体验,没有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觉,是写不出如此智性而简洁、看似无技巧实属大技巧的诗作的。
第三,注重新写实主义诗歌技法探究,完美实现了以诗托物言志
对诗人的解读,有必要对这个诗人的诗观和创作技法进行归纳。在我的阅读体验中,诗人马志强的诗歌当归纳入“新写实主义”序列。这个问题有点牵强,但很符合实际。
新写实主义是对“新写实小说”的一种艺术理论概括。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文艺创作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和流派。在当代文学批评中,鲜见有人对诗歌创作用“新写实主义”一词,但并不影响对诗歌创作的评价和衡量。
从写作特点分析,马志强的诗歌作品符合“新写实主义”对现实负面现象的揭露与批判,笔触都有锋芒,刻画的事件与人物也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从写作内容上分析,作品都淡化了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历史背景,避开重大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致力于描写生活琐事、性爱心理和生命冲动;从诗歌语言上分析,他的诗歌语言很独特甚至是独创,有很强的汉语言文字的跳跃性,字词间的组合有很强的张力。
我在其作品中,也发现了诗人“真诚书写,真情呐喊”的诗观。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在风中,唯一能与我对话的只有诗,也只有诗,才是我的唯一。我不能忘记入学时到北京由于我跟现实生活距离的落差而写下的第一首对自然和人生略作思考的诗《一粒红枣》:
阳光吻秃了树梢
小鸟开始筑巢
幼小的生命
依然坚挺
沐浴在萧瑟的秋风中
流浪的诗人
把生活的面纱撕碎
洒在地上
又拢起一地不解的眼神……
是的,生活不是诗,而且诗歌也不能维持生活。在八十年代,诗受到社会的宠爱,因此诗人也很吃香,毕竟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而现在,人们由于物质生活的浮华和物欲的横流,在人性中的那一点残存的善也消失殆尽,快节奏的生活,人们能干的是什么?这些已经没人去思考,而有更多的人去关注性、欲和一切与金钱密切相关的事物。诗也“沦落为大街上的一张纸片/不如一斤老芹菜值钱”(李小雨语)。
面对自己的诗歌理想,马志强在寻找,他对外寻找的是海涅、里约克、波德莱尔、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在国内,一方面是向优秀的军旅诗人峭岩、朱增泉、王久辛、马萧萧、刘笑伟、石一龙……等人学习,一方面是向诗坛的不朽神话、“麦子诗人”海子学习。
海子是马志强的诗歌偶像,他曾说:“海子,是一个诗歌的神话;一个与诗史永远相关的诗人……建构了一个关于海子的神话,那就是关于诗的本真及历史的思考与追寻、关于汉民族心理界限与死亡肉身形式之间的暗示和象征、解构与重读生命的零点的安祥从容与摆脱人世尴尬的精神处境。”甚至,对海子一次次吟唱“太阳”“麦子”“儿子”的赞歌,认为是海子“在一切生命以及希望的意象中了解自己,确认自己,我认为这是海子对自己的负责,对诗的负责和对人生的一次否定和嘲笑。”
著名评论家张方先生说过;“意象构成诗歌基本美学单元的论断大体上已成为新诗创作者们的共识,诗人的现场感受与潜伏心理都普遍地被归入意象的范畴,意象也因此具备了超越诗人本体认知的社会文化功能,这种功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扩大了诗人的主体性,进而促成了诗人审美经验的升级。”
据此分析马志强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对意象的运用和创作是娴熟而毫无节制的,进入诗歌创作,他的思绪时而是冷静地思考,时而是疯狂的呓语,这在他的诗集中都可以寻找到这样的印证。
比如在诗集《苍茫本部》第三辑《诗歌现场》中,他就创作了《语言是神内思的象征》《冥想》《经历正在经历的事件》《人作为人,及其背后的支撑》等诗歌,出现“死亡、苦难,没有正大光明的名称/而阴谋诡计总靠个别人得逞”,或者“诗已被唐人写尽/话也被伟人说完/独留许多尚不能填补的空隙/如王国维、昌耀、海子”等诗句,意象大开、思绪狂放、语言狂野,显然与平时阅读的其他军旅诗相差甚远。
著名军旅作家齐小才对马志强的诗歌创作有过一度中肯的评价:“轰然的杂乱里有一种严密的逻辑,一种自己相当清晰而容易给读者千万感觉(视觉或者心灵)混乱的特殊意象与情绪”。如此理解,也正阐释了他诗歌创作的独特之处。
马志强诗歌创作,正如著名评论家朱向前先生说的那样:“他的写作淡化了题旨的确指性,冲决了题材的严格界定,而强化了诗的意蕴,拓展了诗意空间。”
结语:“诗之毫厘”,“妙”之千里。一首诗被写出之后,这首诗便脱离了作者的“管制”,而成为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艺术生命。我们必须把一首诗当作一个活的生命来看待。正是诗歌的这种独立性给诗歌作者带来了喜悦和痛苦。
诗歌的独立性来自于诗歌的语言本身。因为诗在言说,每首诗歌的语言,它不仅对每一个读者在言说,同时也是对诗作者的言说。诗言说,正如海德格尔分析的那样,是“语言说话”,语言何以能够说话,并且这种能够“说话”的诗何以“能够掩盖诗人这个人和诗人的名字”(海德格尔《语言》)。从海德格尔的这种追问中,我们不由地感觉到了一首诗歌的强大和一个诗作者的虚弱。
马志强对这种“虚弱”之症的领悟尤其敏锐,他高蹈的书写之姿和低调的生活之态,亦真亦幻地交织着一个西部军人的豪情与一个当下男性的隐痛。其人其诗,游而不离、漂而不浮地折射出一片苍茫的心灵镜像。
姑且慕容:文学青年,爱好诗歌创作,出过诗集,发过短文,在书山文海,期待与您相识、共同前进。

张阳一
